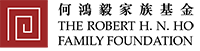遺失與重逢:敦煌石窟西遊記
文:駱慧瑛 |2016-06-22
道士王圓籙(1851-1931)於清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發現了「藏經洞」,其後變賣洞中發現的文物來籌募經費,用作修葺莫高窟,後人對他毀譽參半──一些人視他無知,平賣國寶,他辛苦籌得的經費,用作修葺佛像,卻因水平不如前朝,令佛菩薩像反而面目全非,痛心不已;部分人認為因他的變賣,珍貴文物雖流散世界各地卻倖得保存,免了文革一劫。到底王道士所作,為我們帶來甚麼影響?
開啟藏經時光門
儒、釋、道三個思想體系自古影響華夏民族的社會生活和思想價值。佛教藝術與佛教義理,一體兩面,互相推動、互相成就。佛教藝術對弘揚佛教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國佛教藝術為弘法而創作出大量高水準的作品,可惜這些遺珍的載體,中原的古寺名剎,多因天災或人禍而消失,大量佛教藝術也隨之失傳於世。
唯開鑿於僻遠山崖的佛教石窟寺,雖歷盡滄桑,尚得以保存。敦煌佛教石窟寺,除了最初樂僔法師原意作禪修之用外,[1] 敦煌因處邊陲要塞,其後發展成為中古絲綢之路的樞紐,中西兩方人流和物流的重要集散中心。從四至十四世紀,敦煌一地擔當著政治、軍事、外交、經濟、文化、藝術、貿易、宗教等各方面的責任。這些中原與外界的穩守與交流之間,衍生出連綿千年的佛教藝術奇葩。敦煌這座佛教藝術聖殿因時移世易,國力及版圖的變化、海上絲路的蓬勃興起等,至明朝嘉峪關[2] 建成,敦煌從此被遺忘於塞外。瑰寶被埋於黃沙風雪中,寂然於歷史的角落數百年。


至二十世紀初王道士發現藏經洞,開啟了敦煌石窟寺的時光門,內藏四大文化、六大宗教及十多個民族文化的書畫文獻,加上敦煌石窟群本有保存的735個洞窟、45,000平方米壁畫和2,000多身彩塑及五座唐宋窟檐,為世上現存較完整、內容最豐富精美的佛教藝術遺珍。因藏經洞的發現,出土了四至十世紀的文書、剌繡、絹畫、紙畫等五萬多件文物。文書中大多為漢文寫本、少量刻印本。漢文寫本中九成以上為漢文佛典抄經,其餘有傳統的經史子集和地方官私文書等。漢文以外,有古藏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于闐文、龜茲文等多種已失傳或近失傳的少數民族文字。這些得以重見天日的中古遺珍,是古絲綢之路上各族文明交流的唯一較完整見證,中古盛世景況再度得以重組重現。各國學者聞風而至,各取所愛回國,在世界的學術舞台上紛紛發動研究敦煌文獻及其佛教藝術的熱潮。藏經洞的千古文獻和石窟寺中的部分壁畫和塑像,亦因而流失四散至世界各地。
王道士所作,認同與否,歷史是改變不了的;可變的是將來。保育工作為目前最迫切,這些敦煌佛教藝術,顯示了各古文明的互相融合:印度犍陀羅而來的希臘和羅馬、中東與波斯、印度和中國。這些千年寶物,自出土後不斷在損耗,如奉在我們手中的沙粒般秒間流逝。1987年11月,敦煌莫高窟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再度得到世界關注和愛戴。樊院長前瞻且果敢,1989年以來,敦煌研究院開始與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合作保育工作,長年進行複雜而艱辛的古蹟修復。他們不懈努力、合作無間,至最近有了豐盛的成果,並與大家分享。
絲路上的千佛國
歷史不能重組,文物可以。《敦煌石窟寺:中國絲綢之路上的佛教藝術》(Cave Temples of Dunhuang: Buddhist Art on China’s Silk Road)大型展覽,2016年5月7日至9月4日於美國洛杉磯蓋蒂中心(Getty Center)舉行。展覽由敦煌研究院(Dunhuang Academy)、蓋蒂保育研究所(Getty Conservation Institute, GCI)及敦煌基金會(Dunhuang Foundation)等機構策劃;何鴻毅家族基金(The Robert H. N. Ho Family Foundation)為首席贊助機構。展品包括由英、法等地四家機構借出藏經洞中有關宗教和俗世的文獻和文物,內容豐富多樣。除佛教文獻文物,並有關祆教、景教等文獻;也有粟特文、古藏文、古突厥文、希伯來文等文獻,非同凡響。這些文獻的內容不僅涉及宗教範疇,還有合同、私人信件、占卜書和地圖不等,難得一見。
由大英博物館、大英圖書館、吉梅博物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借出的畫件和文獻,呈現古代石窟寺中多樣的跨文化藝術風格和各朝代佛教圖像。在珍貴展品中,有自藏經洞出土的唐代印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經於姚秦時期(384-417年)由三藏法師鳩摩羅什(Kumārajīva)從梵文譯出,上印有咸通(公元868年)年間製,是世上現存最古老而完整的印刷品,此珍品首度於美國展出。
是次展覽設有三個精心營造的複製窟(第275、285和320窟),它們完全忠於石窟現狀而繪,呈現石窟精美但危脆的狀況,由敦煌研究院的藝術家長期精心繪成。第275窟中有大型彌勒菩薩(Maitreya,又稱「未來佛」),以及早期佛傳、本生故事於壁畫上;第285窟是莫高窟有明確紀年以來最早的一個洞窟,建造於西魏大統四年(538-539年),洞窟大型,壁畫用色斑斕,將印度與中國本土神祇融入佛教,內容獨特豐富;第320窟則建於八世紀,是盛唐的代表窟之一,窟頂藻井繪有富麗的團花(牡丹圖案),四周環繞著裝飾華美的垂幔與千佛圖像。




另設有最新以三維虛擬實境投影技術,立體地呈現第45窟中一鋪完美佛像,相信能令觀者儼如置身於石窟當中,與佛菩薩接心。透過最新科技來支援,能更有效率地把千古藝術精品呈現出來,是再一次超越時空的體驗。2,500多年前,釋迦牟尼佛發現了生命真理,宣之於世,透過絲路由印度傳入至中國。窟中精緻具動感的佛菩薩像,完美無瑕地呈現這一種大乘佛教精神。當你走進洞窟的一刻,成就了佛、菩薩和眾生的聚首一堂,等無差別皆有成佛可能,有離苦得樂的一天。公元前六世紀印度、公元八世紀中國、公元二十一世紀美國,皆因這份佛緣,而在此時此地連貫起來了。
人的五官六感,自出生以來,不斷向外索求,納入知識,經思考和經驗累積而成智慧;同時要守心,不被外間聲色所惑,趨向沉迷。敦煌壁畫中,呈現「世間」和「出世間」的各種景象。見壁畫,觀佛國。不同朝代的演繹,不同淨土的版本──魏晉的優美儒雅、隋唐的莊嚴氣派、宋元的成熟內斂,都是我們的自選空間。石窟和壁畫是虛擬的佛國?還是,這器世界才是虛擬的,如火宅?[3] 我們得趕快脫離這輪迴之苦,勤修悟道,到彼岸佛國去,涅槃為樂。
敦煌石窟西遊記
姑勿論王道士所作是功或是過,世間事物本是「成、住、壞、空」,人的身體與心念也是「生、住、異、滅」,變幻無常。自然或人為的損耗,緣聚而生,緣散而滅。如是來,如是去,不必喜,不必悲。箇中過程,都是為了自己和他人,今世或來世,累積智慧和福德因緣。這些散失於世界各地的敦煌寶物,以英藏最多,法藏最精。它們在世界各重鎮與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結緣,續其千年傳統,默默承擔著跨文化交流的使命。百多年後,這些自藏經洞出土的文物首度重逢。


敦煌——這規模龐大,豐富多彩、獨特稀有、脆弱易碎的人類文明寶藏,得世界各地的有心人努力保護。敦煌研究院王旭東院長近年繼續與全球各地頂尖機構和各領域專家合作,以最先進科技和最真誠心念,對宗教、人文教育、文化藝術等方面作出貢獻。研究學者、贊助大德、畫師和工程師等,不為各取所需,而是各展所長,無私奉獻以達保育敦煌使命。留名與否,都是或深或淺的修行人。他們是現實中的菩薩和天王,為度化眾生而來的菩薩,為保護而彰顯大能的天王。
佛陀在世時代透過言語口傳弘法,佛入滅後,僧侶透過文字記載和圖像啟示,讓佛陀開示的智慧得以流傳,乃至現今我們透過高科技、學術研究等來支持,用願力和毅力所成就。從古至今,無論是書法習字、描線繪畫、誦經聞法、助印經書、開鑿石窟、弘法利生、贊助展覽、修復文物、撰寫論文等,皆是修持,皆具功德,為更好來生作資糧,為成佛多種善因緣。這種個人修持或團體合作,都在無常的時間洪流中,本著「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精神而盡一己力,聚緣和合,成就大眾得聞佛法的機會。一切所為,皆為法寶得延續,慧命得流傳。由佛陀傳給各代高僧,至今天的你和我,我們傳出去給將來的他和她,不分種族與國界,延伸至另一個千年。
佛教從天竺(印度)西來,經西域(中亞)傳入敦煌至中原。至今二十一世紀,在這近乎不受時空限制的年代,敦煌以不同形式擔任著同一重任。把人類文明、精神意象,以最優美的形態呈現,傳至世界各地,由當初的「西來」接引,至今天的「西去」弘揚,如佛陀般「如來如去」,將無上甚深微妙法,透過藝術呈現,令遠方得聞,廣度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