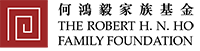說文學之美:品味唐詩,感受被祝福的人生
文:黃首鋼 圖:有鹿文化 | 2018-11-02

中國文學中最深入民間的題材,除了小説外,相信是唐詩了。
大部分中國人總會隨口背出幾首如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等的作品,那可算是現代漢人還保留住淺淺的文化回憶。感恩一班有心人的努力經營,讓我們還知道如何欣賞和珍惜這些寶藏!
最近偶閱蔣勳先生的《說文學之美:品味唐詩》,知道他「從小在詩的聲音裡長大,父親、母親,總是讓孩子讀詩背詩,連做錯事的懲罰,有時也是背一首詩,或抄寫一首詩。」幸而那不曾造成他的童年陰影,今天我們才能從這本整理他有關唐詩的讀書會錄音中去探索中國文學發展的脈絡、體會大唐盛世的宏大氣魄,以及品味中國傑出文人對人生的反思和感悟。
蔣老師對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李商隱等唐代詩人的作品都有深刻的分析,加上他自身的美學修養及對生命的體悟,令讀者閱時如春風拂面。書中一些句子,都值得再三回味。
他很細膩地形容詩的發展:
「詩很像一粒珍珠,它是要經過孕育和琢磨的。我們的口腔、舌頭、牙齒、嘴唇在互動,像蚌殼一樣慢慢、慢慢地磨,磨出一粒很圓的珍珠。有一天,語言和文字能夠成為一首華美的詩,是因為經過了這長期的琢磨。」[1]
「文學史有繼承的關係,和大自然一樣有春夏秋冬。唐代是花季,花季之前一定是漫長的冬天。在冬天,被冰雪覆蓋的深埋到土壤裏的根在慢慢地做著準備。」[2]
經蔣老師的引導,我們像重新認識唐詩這位老朋友,亦擴闊了我們的眼界:
「唐詩給我們最大的感覺就是空間跟時間的擴大。」[3]
「空間和時間的擴大,使原本定位在穩定的農業田園文化的漢文學,忽然被放置到與遊牧民族關係較為密切的流浪文化當中。[…]許多唐代詩人最大的特徵幾乎就是流浪。在流浪的過程中,生命狀態與農業家族的牽連被切斷了,[…]安史之亂以前,李白與王維都有很大的孤獨感,都在面對絕對的自我。在整個漢語文學史上,面對自我的機會非常少,因為我們從小到大的環境,都要面對親族關係,生活在一個充滿人的情感聯繫的狀態裡。[…]人情愈豐富,自我就愈少。我們讀唐詩時,能感受到那種快樂,是因為這一次『自我』真正跑了出來。」[4]
蔣老師指出唐詩「從邊塞詩又發展出與南朝有關的『貴遊文學』,(它)非常敢於描述生活上的揮霍與奢侈,非常華麗。[…]誇耀生命的華美,頭上的裝飾、身上的絲綢、生命中的一擲千金,如李白〈將進酒〉說的『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 唐朝是一個覺得美可以被大聲讚美的時代。」[5]
他認為我們感覺唐詩迷人,「也許是因為剛好唐詩描寫的世界是我們最缺乏的經驗,在最不敢出走的時候去讀出走的詩,在最沒有孤獨的可能時讀孤獨的詩,在最沒有自負的條件時讀自負的詩。[…](他)在翻閱唐朝歷史的時候,覺得每個生命都是在最大的孤獨裡面,實現了自我完成。」[6]
不過,他形容「唐朝就像漢文化一次短暫的度假期,是一次星空下的露營,[…]最後還是要回來安分地遵循農業倫理。[…](雖然)回想起來,往往一年最美的那幾天是去露營和度假的日子,唐朝就是一次短暫的出走。」[7]
他也經常形容唐朝是花季。他介紹唐詩〈春江花月夜〉時,以武則天欣賞討伐她的駱賓王之才華為例,「在現實當中,事關政治的爭奪;可是在美學的層次上,每一個生命都可以欣賞另外一個生命,這才是『花季』出現的原因。所謂的花季,就是所有生命沒有高低之分,春天、江水、花朵、月亮、夜晚,這些存在於自然中的主題,偶然間因緣際會,發生了互動關係,可是它們又各自離去。它們是知己,也是陌路。[…]這裡面的生命意象,沒有一點小家子氣的糾纏黏滯。」[8]
至於他感歎「很多儲存在心裡的零散、破碎小片段,在生命的某些經驗中會忽然活過來,活過來不是因為我們閱讀它,而是因為我們忘了它。」[9]及總結「詩是遺忘的過程」,耐人尋味。或者從他隨著的補充,找到一絲線索:「忘得愈乾淨它愈容易跑出來跟我們對話。我相信好的詩不是專業研究的物件,它經常脫口而出,契合了生命在剎那的狀態跟經驗。」[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