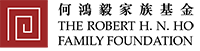茶是一面鏡子,反照出我們內心──專訪香港茶文化院院長葉榮枝(上)
文:鄺志康 圖:Tim Liu | 2018-12-14

「銚煎黃蕊色,碗轉曲塵花」[1],教詩客愛、僧家慕的茶湯,是天地之鑑,是萬物之鏡。品茗是道,是形而上,是精神面貌的展現,是我們為追求生活背後那一點真理的光芒而作的努力。「喝茶是生命的事!」葉榮枝開宗明義說道。他除了是樂茶軒的創辦人、香港茶道協會會長、香港茶文化院院長及中國茶葉學會理事外,還被譽為紫砂之父。茶文化在香港方興未艾,早前乘著香港茶文化院成立的因緣,來到位於金鐘的樂茶軒,點了一杯茶,聽前輩訴說茶與他的故事。
葉榮枝爽快的坐在茶席前,手勢老練、俐落,不著痕跡。一盞熱茶,旁觀世態炎涼;古有煮酒論英雄,今有烹茶論時勢,葉榮枝從香港最近幾年對生活感到迷失的情況談起,認為這十分符合了經典中對末法時期的理解和詮釋:「全球現在陷入崩潰的危機,大國互相較勁,有些小國也陷入瘋狂狀態。」面對這些近乎混亂的情勢,他不禁端起茶杯再問一聲:「孰以致之?」我相信若要解憂,不止杜康。茶為萬病之藥,古人早已有論述。
茶是一面鏡子
葉榮枝講學,多從文化角度切入,但畢竟是很籠統的說法,時至今日也沒有哪位專家或學者能精要地涵蓋文化在不同語境下的各種意義。這讓我們聯想到,在中國哲學思維中,「道」和「器」常並列而談。若道是抽象的,那器就是具象的;道是精神,那器自然是物質。雖然道器思想是從道家及儒家的角度出發,套用在佛教,可以看成真實與方便,可以理解為體(本體)及相(表相),只有道器並濟、並用,方能恰到好處。茶道自當如是,像陸羽在《茶經》中說「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行儉德之人。」精行、儉德──行為合符社會規範,品德恪守傳統道德,就是茶之道。仔細思維,這還是君子之道、修行之道⋯⋯那不正正和葉榮枝所說的「喝茶是生命的事」相吻合嗎?「曾去過一個茶博覽會,主題是『器以載道』,我以為器乃道的體現,到底是否一定要分主、次,我猶有保留。茶是一面鏡子,反照出我們內心。」他娓娓道出日本茶道始祖千利休和大名豐臣秀吉的一段茶道故事。戰國時代來到尾聲,豐臣秀吉於1587年就任關白(攝政)平定九州,基本上統一日本,是當時最有實力之人。他為了慶祝並向朝廷及京都民眾展示權威,於當地北野天滿宮舉行了「北野茶會」(日稱:北野大茶湯),並下令全國茶人,不論身分貴賤、不論階級出身,都可前來喝茶或展示茶藝。為了給天皇奉茶,豐臣秀吉花了近半年的時間,用了上百斤黃金,建造了一所著名的黃金茶室,裏面所有的茶具都是用黃金製造。在茶會第一天,天皇來到,驚為天人,十分認同秀吉對自己的尊敬。然而到了第二天,是千利休主持茶會,他竟然請天王帶到山郊一間簡陋茶室,那裏只有只有兩張榻榻米。千利休只用普通的陶碗,為天皇奉上他的草庵茶。據說天皇吃茶時,感動得流下兩行眼淚。「為甚麼會有這種分別?黃金之器也好,破舊的陶碗也好,茶還是那杯茶。隨著器物的不同,映照出我們內心的不同狀態。」

為茶壺注入生命
今人喝茶,多著重外相的展示──茶器如何精緻、茶席設計如何華美。然而茶道絕非台上作表演的藝術,更不只是一場繁瑣的儀式。有不少人只追求悅目的茶具、華麗的服飾,把茶席視作個人美感延伸的舞台。 明代馮可賓在《茶箋・茶宜》中,提出了品茶有十三適宜:無事、佳客、幽坐、吟詠、揮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會心、賞覽、文童,其中只有「清供」及「精舍」是泛指茶席擺置。其餘十一宜,以「無事」為首,品茶人心中不可存功名利碌之想,當下一刻須怡然自得,心無罣礙,否則茶再好,也不過是驢飲[2]。又如「佳客」,說的是茶客最好以博學多聞、風雅睿智之士為佳;再如「清靜」,更是要求茶客與茶主人心境清澈澄明,內心不生波瀾,這些都屬於精神層面的。我問葉榮枝,到底今人是否距離這種境界越來越遠呢?「也不一定的。我看還是有辦法觸及到的。《心經》說色即是空,形式固然是表象,但是否真的代表不能捉摸?其實諸法是如如的,是反應真實。一個人他當下那刻,內心的狀態如何,是會通過不同途徑顯現。從喝茶的角度看,那是對個人修養完成的一個進程,你的內心如何,你的精神面貌也如何,而這些都會從你泡的茶流露出來。」
談到和茶的因緣,葉榮枝相信和絕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都是自幼開始,多是跟著父母一起上茶樓。相較現在小朋友往往是被逼飲茶,談不上是享受,他那個時候則平淡多了,更像是一種生活習慣。「我父親是中醫,每逢過節都會特別泡普洱及一種叫神曲茶的藥茶給家人,因為它們都清純正氣,是好東西。那些多是日常規律,反而印象不深。倒是很期待上茶樓,最記得是多去瓊華酒樓(現在改建成了瓊華中心),去吃窩蛋牛肉飯。每次知道第二天是要上茶樓的,往往會徹夜難眠,急不及待清晨第一時間便起床。」葉榮枝小時候對傳統茶的感覺大抵是這樣,主要是和喜愛的食物連結在一起。後來到了小學五年級,和同學一嘗絲襪奶茶,更是愛不釋手,經常留連學校附近的茶餐廳。「時至今日,每天早晨我一定要來一杯奶茶,否則當天辦事全無起勁,像熄滅了的火。」
及至中學時期,他迷上了紫砂茶壺;到了進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因緣巧合下認識了古筝演奏家陳蕾士。陳蕾士是潮州人,而潮州又以功夫茶這個茶俗見稱。功夫茶必定是要小杯的,最好是用烏龍茶,其中較常見的一種沖泡是斟滿了一杯再斟第二杯,接二連三,輪流不停地循環斟茶,是為「關公巡城」。陳蕾士愛音樂也愛茶,據葉榮枝憶述他每天都要到山上打泉水,邊泡茶邊聞鼻煙,那種中國文人雅士的魅力,深深烙印在他腦海中,而茶亦漸漸成為他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驅使他從經濟學系畢業後,再修讀藝術系。
修畢藝術系課程後,葉榮枝來到中大文物館當研究助理。有一天羅桂祥來找館長,說想請人研究他的紫砂珍藏。羅桂祥是誰呢?維他奶的創辦人。當時香港人普遍對紫砂茶壺認識不多,剛巧葉榮枝自幼對茶壺有濃厚興趣,館長便委派他跟進,二人一拍即合,研究成果更衍生出1979年在文物館舉辦香港首個茶具展覽。誠如葉榮枝所用,道器互為表裏,要了解器具,便先要掌握道體。他由此入門,環環相扣,從茶具追溯到茶葉、茶歷史和文化,此後和茶正式結下不解之緣。「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決定一起去宜興,了解紫砂壺的精緻工藝及背後蘊藏的深厚文化。當然是大開眼界,但同時也好奇為甚麼沒人特別作買賣。」原來是因為壺價太低廉了,普通的三、五毫子價格,如顧景舟這種一代宗師的,也賣不過五元。葉榮枝回來後,決心引進紫砂到香港,於是和羅桂祥合作成立了一家公司,正式做起茶壺的買賣。「當時內地還未開放,崇尚去個人化的風氣,所有工藝品不得署名標記,是我們重新推動在壺上刻印款的習慣,畢竟是大師的作品便應該有獨特的記認。」他說的是壺底上的身份證。壺底原先只是展示造型風格及代表壺的功能性,最初壺底是光禿禿甚麼都沒有,到了後來加了「中國宜興」,到現在各款鈐印,除了造壺者名號外,還有店號、詩詞等,百花齊放。今人再度重視壺底印款,開啟了紫砂收藏的熱潮,葉榮枝應記一功。「說起來這種文人雅士的玩物心思也是虛幻,但不能否認,它為茶壺注入生命。」
有壺又怎能無茶?大約在八十年代後期,葉榮枝認識了一位來自安溪的同事。隨著國家開放,他們得以參觀當地農村,認識茶農。「當你親自觀賞到大片大片的茶園時,你會頓然感覺到茶是天地間的靈氣所在,甚至天、地、人三個元素都聚集於一小片綠葉之上,含藏諸多因緣在其中。山勢高一點和低一點,種植出來的茶葉韻味也自然不同;天氣則一般是春天最好,生機勃勃,一年的成果只看那個時候,而且最好吹北風,陽光充足,種出來的茶一定好喝;人也要講求技術、手藝、用心、管理⋯⋯每片茶葉不正是眾緣所在嗎?」自此他每一種茶都盡可能仔細研究。他笑言現在學茶幸福得多了,除了茶藝班,還有成千上萬關於茶的文字任君選擇,不像他當時要從《茶經》及其他原始文獻中爬羅剔抉,才能知之大概,還得親自跑遍大江南北,方有所成。閱歷夠了,對茶的感悟也昇華到另一個層次,葉榮枝認為是時候創立自己的茶館了⋯⋯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