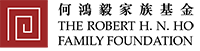攻琴如參禪──古琴申遺成功十五年,反思佛教對中國琴文化的貢獻與兩者間之衝突
文:陳耀紅 圖:陳耀紅 | 2019-03-08

古琴申遺成功,已進入第十五周年。自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宣布古琴成為「人類口述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後,無論中外,愛好古琴的人復多,不時亦見到僧人鼓琴。事實上,「攻琴如參禪」,琴文化與佛教義趣有共通之處;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不久便已開始與古琴文化結緣。
佛教是在印度貴霜王朝鼎盛時期(Kushan Empire,大概由公元30年左右,至公元250年前後,其疆域西至塔吉克、裏海一帶,東抵恆河流域),隨著商業貿易進入中國,時為東漢(公元25 —220年)時期。這個時期,古琴音樂流行於中國的貴族與士大夫圈子,例如東漢末有名士蔡邕及其女蔡文姬,三國時代有諸葛孔明、曹植等,都是古琴高手。
至於佛教方面,漢桓帝(公元147 — 167年)初,已有安息國(今伊朗)太子安世高法師東來,他「博曉經藏,尤精阿毗曇學,諷持《禪經》」(見《高僧傳》),而佛曲唱誦分「諷詠」與「梵唄」兩部分,皆有音樂性,因此,估計印度佛教唱誦漢末已傳入中國。稍後,印度貴霜朝僧人支讖法師則於桓帝末年抵達洛陽,其弟子支亮法師的在家徒弟支謙居士,也是一位移居漢地的大月氏(印度)人後裔。支謙居士於漢獻帝末年隨族人避居江南,因博學多才而得吳主孫權拜為博士(官職),《高僧傳》有載:「謙以大教雖行,而經多梵文未盡翻譯⋯⋯乃收集眾本譯為漢語,從吳黃武元年至建興中,所出維摩大般泥洹法句瑞應本起等四十九經,曲得聖義,辭旨文雅又依無量壽中本起,製菩提連句梵唄三契。」(見〈康僧會〉條)《高僧傳》記載的這些早期在中土弘傳佛法的僧俗,不論來自中外,都博學多才,且通曉梵唱,並遊走於民間與官場,很難想像他們完全沒有接觸過與參禪有共通意趣的古琴音樂。
佛教僧人對古琴文化傳播貢獻良多
不過,最有趣的是虞炎獲贈古琴的故事。虞炎是南朝時期的一位將軍,也是一名詩人,存世有《玉階怨》一詩。炎因遇南齊文惠太子(南齊武帝之子),而官至驃騎將軍。南北朝時期,南齊(公元479 —502年)因宰輔竟陵文宣王蕭子良的倡導,佛教曾光大盛極一時,齊武帝蕭賾和豫章王蕭巍皆禮佛敬僧。虞炎少年時登遊於秦望山(位於浙江省),遇獵人捕獲一鹿,鹿向炎悲鳴,炎不忍,買而放之;後炎經山下,遇一陌生人,贈炎一琴,而贈琴人瞬間失去蹤影。琴背有字,但不可辨。多年後,炎以此琴示沈約(以詩聞名,且精研佛經),沈約反覆閱覽,認為是「土離塵曾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共十二字。此時,虞炎已為文惠太子所重,拜為驃騎將軍。沈約不禁歎其異,因為「土離塵」即鹿字,「曾獲貝」 為贈字。虞炎始悟獲琴及遇文惠太子皆放鹿之因果報應。這個故事見於宋虞汝明《古琴疏》。此外,清代《天聞閣琴譜》的〈紀事〉亦有載。
古琴史上除了具有這種帶著佛教義理的故事外,歷代亦出現過許多著名的琴僧,尤其是由隋唐開始,有關琴僧的記載日益增加,包括如李白、白居易等的詩作中,都有涉及琴僧的內容。此外,宋朝以降,琴僧對古琴傳承影響不小,其中如夷中法師、知白法師、義海法師、則全和尚等的事跡,在文獻中多有記載,則全和尚還著有《則全和尚節奏指法》;而至今仍孕育著琴人的廣陵派(例如張子謙、 劉少椿等)中,便有編著《枯木禪琴譜》的空塵法師,他的學生黃勉之是清末重要琴家。黃勉之為求空塵法師收其為徒,還落髮為僧,入了空門兩年。空塵法師的佛門琴弟子還有肇慈法師、印恒法師,和起海法師等。至於空塵法師自己,他最早的一位古琴師父,是菩提院長老牧村法師;而牧村法師的琴師父是先機和尚;先機法師的琴弟子中,僧道皆有,僧弟子包括問樵法師。問樵法師的琴弟子秦維瀚除編撰了廣陵派其中一部重要譜本──《蕉庵琴譜》外,還有徒子徒孫輩出,成就廣陵一脈至今,而他的徒子有僧有道有俗,僧人包括了四大琴僧雨山和尚、蓮溪和尚、皎然和尚,及普禪和尚外,還有聞溪和尚與海琴和尚,其中,海琴和尚傳廣霞和尚。在2013年去世的名琴家林友仁之女林晨所著的《觸摸琴夫──近現代琴史敍事》中,1919年8月怡園琴會、1920年10月晨風廬琴會中,廣霞法師都有出席並彈琴。此外,1937年10月出版的《今虞琴刊》琴人問訊錄中,仍見雨山法師與廣霞法師之名,及其地址、藏琴藏譜等。
至於香港,在黃樹志《20世紀香港琴學之發軔與傳承》中,1957年4月,當時避難南下香港的文化人在志蓮淨苑舉辦第四次琴棋書畫雅集,共五十餘人,「盛況空前」。據此文表列,沙田萬佛寺於1956年亦舉辦過雅集與琴會活動,萬佛寺創建人月溪法師在琴會上彈了《陋室銘》;此表還記述,月溪法師在國內曾造琴及授琴弟子。而在萬佛寺的網站介紹開山祖師一欄,指月溪法師「善七弦琴,游必㩗琴隨身」。
香港志蓮近年亦開辦古琴有關科目及音樂會。在志蓮授琴多年的名琴家姚公白的師承中,亦與釋門有密切關係。其中淵源,有心的讀者可查閱我2015年寫的《釋門琴與姚公白》。
對外方面,韓國與日本的佛教最早主要經中國傳入,古琴音樂大概也同期進入朝鮮和日本。日本宇多天皇時期(相當於唐昭宗時期)的《日本國所見書籍目錄》載有當時庫存的中國多種琴書。現存世最早的琴譜《碣石調.幽蘭》曾長期收藏於京都一家佛教真言宗的寺院。至今,位於華嚴宗本山東大寺內的正倉院與日本不少佛教寺院仍藏有來自中國歷朝的古琴。此外,明末清初,由杭州東渡長崎的東皋禪師曾令中國古琴音樂在日本大盛。
佛教音樂在古琴中的發展受限制
以上事例在在顯示佛教僧人對古琴文化的傳播,貢獻良多。不過,涉獵過佛教史的人都會知道,佛教在中國須與本土土生的儒道文化有所協調,遇到比較極端的人,還會出現衝突。古琴史在這方面有具體的佐證。例如,明朝萬曆年張右袞所輯的《陽春堂琴經》在卷九〈大雅嗣音〉便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僧名覺(道)者,學琴於道人白隺子之門,隺子惡而不受。僧不悅。隺子曰:怪哉,釋氏之學出于西方夷狄之教,琴乃中國聖人之道,非爾所宜也。竟不傳。」
同是明萬曆年間刻印的《重修真傳琴譜》亦有記載此事。《重修真傳琴譜》撰錄者名楊表正(約公元1520 — 1590年),他在〈樂不妄傳論〉一節中,整節對釋門極盡詆毀,還有「……張橫渠過郢陵泛,童子挾琴而隨遇一僧以手捫其琴;曰,琴不倖矣。遂棄之於流水」的講法。作者蔑視釋門所持的道理,除了因其是夷狄之學,還因認為佛教不符儒學方面的「聖人之道」之故。
著名的荷蘭籍漢學家高羅佩(R.H. van Gulik,1910 — 1967)也是一位古琴家,他亦發現了古琴界中有這種排斥佛教的現象。不過,作為荷蘭外交人員,他在1939 — 1941年間著作的《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An Essay in the Ideology of the Ch’in)中,只是嘗試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法,來表達他對這現象的一種 「折衷立場」。一方面,他把拒斥佛教的,說成是局限於有門戶之見的道家中人;另一方面,在打道家五十大板的同時,亦指維護僧人彈琴權益者中也有極端分子,他寫道:「沙門子不宜鼓琴」 一說,「自然遭到強烈反對,某些佛教徒的反應更是激烈,他們試圖證明古琴是源自印度,因為佛經裏有這樣的說法。」跟著他提出「古琴愛好者」應有的立場,就是「不會受到極端的道教或佛教觀點之影響」,而是「滿足於在不至於相互矛盾的情況下同時援用雙方的觀點。」(見李美燕譯的版本,另有宋慧文等合譯的版本,意思也大致相同。)
當代音樂學學者、北京中央音樂學院現代遠程音樂教育學院副院長苗建華對這問題的分析則比較全面而深刻。她在《古琴美學思想研究》指:儘管佛教傳入中國後,「……隨著佛教寺院的增多,佛教教義的普及,佛樂在民間有許多建樹,但文人對此的偏見依然根深蒂固。作為文人音樂的代表,古琴美學深受文人輕視胡夷之樂思想的影響,這就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佛教音樂在古琴中的發展」。
今天,儒道等勢力已不如前,古琴音樂亦瀕危,須透過申遺來加以保護。然而,時代雖變,但佛教與其他宗教一樣,隨著人的價值觀偏向用物質為衡量標準,因此亦面臨新挑戰。人間世俗由一種偏執,改為傾向另一種偏執。這就是輪迴的最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