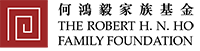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畫家鄭力的山水、園林、禪思
文:鄺志康 圖:Tim Liu、漢雅軒 | 2017-08-29
竹、茶几、花瓶、一扇扇敞開的門窗,共同建構出鄭力別出心裁的園林美學。早前香港漢雅軒推出中國水墨藝術家鄭力個展--「故園心眼」,展出他歷年來的精品,包括2004年於第十屆全國美展獲得銅獎的名作《晴雪》。鄭力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中國畫系山水專業,現在是美院的副教授,同時他也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中國畫院研究員。他的作品曾分別入選百年中國畫展,第八至十二屆中國全國美展,每屆都能獲獎。他的筆觸雄邁有勁,時而靈動時而沉實,其園林畫作,更是別尋蹊徑,為本應小巧別緻的院落增添廟堂大氣。
《西遊記》中的山水啟示
鄭力走上畫山水畫這條路,說來話長,但起點要算是《西遊記》。「《西遊記》中有大量描述山水景象的優美文字,例如孫悟空飛到某個新地方時,吳承恩總會配上描寫的段落,閱讀時都會令我有很強的感應。」那時候他還在念初中,但已深深為那種意境所吸引。長大後投考中國美術學院,想也不用想便選山水專業,之後受師長前輩照顧,很自然的在這一個領域打下了穩固基礎。事實上,他母親也畫畫,雖然主要是電影海報。「自幼她為我創造了有利於探索藝術的環境,至於畫些甚麼題材、怎樣遲,她都不干涉。」
鄭力早期的作品偏向大山大水,現在的則多集中在亭台樓閣、曲徑迴廊,產生這種轉變,源自於他一顆渴望不一樣的心。他年輕初創作的時候,畫壇流行的是畫田園、黃土小景一類的;偏古意的山水,大家都不大想碰。「我承認是有點想刻意走與別人不一樣的路線,人家如果畫小房子,那我便畫大房子。」後來他發現複雜的技巧形式及結構,更合口味,於是便慢慢多畫了園林作品。「越畫得多山水,越發感覺到千篇一律,跟人家都一樣,多沒意思,於是更銳意要走自己的風格了。」只是到目前為主,他都沒想過要帶領甚麼潮流,甚至是反潮流。「身為畫家,就是單純想多給這個世界一點不一樣的口味。這次的『故園心眼』,模式上更像是我個人的回顧展,你可以看到以往的作品,傾向予人飽滿、充實之感,現在的則空靈感多一點。我相信畫家都要經歷各個階段,才逐漸找到屬於自己的風格。」
侘寂美學──以極端細緻的手法來處理粗糙
最近五年他迷上了茶道,收藏茶器方面也甚有心得,又出版了《鄭力的茶室》一書,筆下逐漸染上和敬清寂的神采。他表示,滲透著日式侘寂(わびさび)美學的器具、禪畫,貌似粗糙、不起眼、不對稱,然而仔細看,都是刻意而為之的,是採用極端細緻的手法來處理粗糙感覺。「我們總想把一張畫紙填滿,線條要夠多夠密,千辛萬苦要營造出豪華的效果;但你看日本人,反其道而行,挖空心思來製造大量空白,令你不禁覺得很舒服。這種思路,某程度上對我們有啟發性。」日本的茶聖千利休,和豐臣秀吉是主僕關係,前者亦是後者的茶道老師。有一個故事是說千利休的園子種滿牽牛花,異常艷麗,豐臣秀吉聽說了,一定要去觀賞。怎料第二天他來到時,發現千利休把所有花都砍掉了。豐臣秀吉當然大怒,這不是要捉弄他嗎?原來千利休只留了一朵,插在茶室裏的花瓶中。「他想表達的是,只有一朵珍貴的,這樣便足夠了,其餘的再多的也只是數字上的量而已。中國人素來喜歡繁華、複雜,偏的一定要糾正過來,這兩種思維的對比,是很有趣的。」起初鄭力愛畫工筆,因此構圖的表現密度頗高,從1999年讓他獲得中國全國美展金獎的《書香門第》可見一斑。現在再畫園林,感覺又不大一樣了。

曾於鄭力某些早期作品上,見到他的題款有「大宇居士」及「鹿鳴精舍」兩者。原來當時因緣際會下,他認識一位老教授周昌谷,是浙派畫家的一號重要人物。所謂「二十弱冠而字」,他請周昌谷替他取字;周昌谷按他名字中的「力」,配以大宇為字,取其力之至大者無過宇宙之意。至於「鹿鳴精舍」,則要追溯到台灣故宮藏的五代《丹楓呦鹿圖》。「在讀書階段,我有一段很長時間都在臨摹。這張畫令我聯想到《詩經》『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之句。我很喜歡這種豪華中見真樸的意境,而且臨摹的效果不錯,對我影響也大,便把畫室稱為鹿鳴精舍。」這些,都是較年輕時的事。
無論是九年前的《遊園驚夢》,抑或是去年最新的《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鄭力都力求在作品中表現出如電影般的虛幻情懷,打破傳統園林畫的視覺模式。例如在後者,蘇東坡手持竹杖,杖穿透他的身體,而他左方則有另外兩根竹杖,其中一枝也是同樣穿透他而過,彷彿蘇東坡正從左一路移動到右邊來。「我以前曾在電影公司工作過,也愛看荷里活的出品,例如一系列的大空電影,對我影響也許對單純閱讀來得更大。

一切都是自己的心都作崇
自古在亂世中為求存者,選擇隱退的大不乏人,而當中不少文人畫者在這個時候轉向以藝術來表現自我。我不敢妄斷現今是否屬於亂世,但的確人心不甚安穩,而我也很好奇,作為畫者,鄭力是怎樣看自身乃至自身創作與大時代、大環境之間的關係? 「讓我扯遠一點說,在北京潘家園的舊貨市場,你可以找到大量古玩。九十年代初我去的時候,真品比較多;到現在,膺品多了。我有兩位朋友,他們去了一趟,買回來的都是膺品,很不高興,不想再去。但我不是這樣看的,我去了,買了一件我心儀的物品,下一次還會再去,管它其他都是真真假假。我們也應該以這種心態來看待所謂的亂世,當我內心不把干擾當作一回事時,它又怎能影響我呢?對於必須要面對的事情,你可以選擇痛苦的去處理,更可以快樂的看待它,一切都是自己的心都作崇。」也許因為這樣的原因,鄭力看起來總是充滿信心,臉上經常掛著笑容。
《文心雕龍》很重要的其中一篇是「通變」,談到新舊文風累積及變革的問題,劉勰的討論,亦可套用在藝論上。鄭力相信我們強調所謂筆墨的創新到了最後,其實不會新到哪裏去,事實上任何藝術形式也是如,到最後是要看自己怎樣理解和時代本身的關係。「歌劇《托斯卡》(Tosca),巴伐洛堤唱的跟多明哥和卡列拉斯唱的有甚麼不同? 可能巴伐洛堤某段唱得特別好,而另外一段是其餘兩人更具功架。可《托斯卡》還是《托斯卡》,普契尼的作品不會忽然變成另一個模樣。 」但話又說回來,他相信,即使畫家再反對、再喜歡復古,也不會只畫成跟古代一樣。時代風格肯定是畫家避免不了,然而有些人天生出來就是擁有要超越時代的視野,以致於他三百年前的畫,到今天看來仍然教世人驚嘆不已。「畫家要清楚自己看問題的框架,你站在甚麼高度,便決定你的行為會如何。你的知識範圍到達某個濃度,自然會產生相配合的要求。」像他的《順水圖》,反向臨摹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把原畫景色調轉方向,溯江而上改為順流而下。「臨摹《富春山居圖》,大家都有能力處理,有時可能是你較好,有時是他。如何超越這個模式呢?於是我動動腦筋,要做得好玩一點。黃公望是從田園畫到山林,那我就倒過來從山林到田園,結果還引起不少話題。」在他看來,作畫就是反應個人的素養,他會盡所能畫得最好,至於其他無法控制的因素,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因緣了。
他最後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都不排斥禪這個概念,但若要畫家真的能自在表達禪意,端要看他理解得深不深,還是只嘴巴上說說而已。「舉例說某人畫的畫有書卷氣,那是否就代表他要讀很多書才能達到這個境界?理論上他一定讀得不會少;現在換個角度看,通常閱讀量最大的不外乎是學者、作家,那他們能畫出一幅有書卷氣的畫嗎?答案顯而易見。」在他看來,畫中如何會出現禪意,是無法解釋的,可能畫家天生有慧根,無論他怎樣下筆,那種清脫的感覺都會呈現出來。至於他是否符合禪家的要求,這個他留待觀者只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