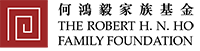姚仁喜 手心眼合一 建構寧靜莊嚴境地
文:鄺志康 圖:Tim Liu | 2016-11-28
對姚仁喜來說,建築是千頭萬緒的事情,一點一線,不容輕忽。即使在紙上盤算得多好,不到落成的最後一秒鐘,他都無法確定作品能如實呈現心目中的形象。此亦如人生的不確定性,比比皆是。
在他創辦的姚仁喜 | 大元建築工場辦公室裏,姚仁喜打趣說,建築給他最大的回饋有三樣:頭髮白了、眼睛壞了、 體力差了。這位台灣著名的建築師,學佛,修習密宗,是宗薩欽哲仁波切的弟子,為他翻譯多本重要著作,將其教法介紹給各地華人,影響深遠。農禪寺水月道場、養慧學苑、故宮南院、烏鎮劇院、巴黎佛光山,作品遍佈全球。在建築中流露充盈詩意,藝術美學與修行融合,輕鬆自在而不強求,做到手心眼合一,成就出別有人間的一片寧靜莊嚴境地。
慢活才是真生活
來到台北,下意識總想拿她跟香港、東京比較,同樣是冶煉多元文化的大熔爐,城市之美除了是生活態度的彰顯外,更照射出文化底蘊的強弱。姚仁喜直認不諱,很多人說台灣是亞洲最醜的城市。原來其實城市跟人一樣,判斷她美醜與否,除了外表還得看內涵。「她是否有趣?有沒有深度?能否給我們驚喜?一座有深度的城市會值得我們不斷探索,我們亦會聽到他們傳達出來的獨特美感。」
據姚仁喜觀察所得,台北這幾年變得較以往從容、自在。十五、二十年前的台北像青少年,處於尷尬的年齡,雖不幼稚但也說不上是成熟,面對很多事情還是有點混亂。「這幾年(台北)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溫和多了,車子會讓人先走,不亂鳴喇叭,因為大家不急了,有一種生活的步調慢慢走出來。」另外他認為台灣人很實際(practical),辦事情的速度是沒話說的,但跟東京這類城市相比,看起來還是欠了點情趣及浪漫氛圍。他經常走在京都小巷,那裏普通人家的花園、圍籬都是用竹子編出來,而綁著竹子的是如假包換的草繩,日曬風吹,壞掉了便換。「不是嘲笑,但在台灣你看到的一定是塑膠繩,然後甚至連竹子都是塑膠,印刷出來的,因為可以使用很長時間,又不用花時間去綁。我們就是這樣的 practical。」
又例如,京都有一家掃把店,三百年歷史,代代相傳。掃把美不美?姚仁喜覺得很難評斷,但社會上有這種堅持把手藝留存下來的事郤很美。實用主義太興盛的城市,生活趣味會逐漸減少,最終一切只餘下平淡。
姚仁喜的結論是,日本受禪宗影響,生活細節已變成儀式。在儀式化的進程下,當代日本人可能不覺得生活的點點滴滴跟修行、正念有關,但他還是注意到例如女士在健身房上完瑜伽課,她們會對空無一人的房間鞠躬才離開。「一旦有了儀式,生活便會慢下來,繼而生成品質。」
香港人走路是有名的快,萬馬奔騰。若說台灣人實際,那我們著重的自然是效率,彷彿慢一點渾身都不自在。每次一步出機場,他的腳步也跟著快速起來,明明不是要趕甚麼事情。「我們常說不浪費時間,省下來多做有意義的事情,乍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到了最後關頭,我們還是會不自覺地一味求快。都養成習慣了, 所以我們賺錢快、工作快,連布施也快。」 事實上慢活才是真生活。姚仁喜特別喜歡約翰連儂(John Lennon)為他兒子Sean寫的歌Beautiful Boy (Darling Boy),當中一句「Life is what happens to you, while you’re busy making other plans.」正正道出生命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每一分每一秒,沒有甚麼安排、計劃,更沒有談浪費不浪費。

我們只是選擇性相信 某些真相
舊時代輕易給我們這種感覺:人人自強不息、守望相助─香港談得最多的便是獅子山下的奮鬥精神;可惜現時家庭和社會結構已漸漸轉變,說同舟共濟, 恐怕對不少人來說十分生疏。政治爭拗更是傷透了大家的和氣。我相信台灣整體在這方面也不差太遠──思想上, 今人愛發牢騷,感覺過去美好的逐一幻滅。姚仁喜說他最近翻閱《莊子》,莊子也常描述自己的時代多麼不濟,之前的孔子更是。「每每有人慨歎時代走下坡,坦白說我不知道是否如此。我們是否投射了一個過分美好的形象到過去,把以前想像得太好,現在理解得太壞?」他主張我們多從哲學角度思考:過去是甚麼?歷史是甚麼?歷史是我們對過去自以為是的投射(projection)。佛陀常教導我們,過去的事便是過去了,只是凡夫想以古窺今,糾結迷執。「像很多法師都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總是在恐懼及期待中過日子。懷念過去、期望將來兩樣都做到了,偏偏忘卻的是現在當下這刻。科學家則走在天秤的另一邊─未來總是美好的,而那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姚仁喜很喜歡意大利導演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作品。貝托魯奇有次接受雜誌訪問時,對方問他想藉著電影傳遞甚麼訊息;他回答,傳遞訊息是郵差(postman)的工作,而不是導演的。「藝術家最好不要有『我要傳達甚麼』 這種想法,這會造成干擾。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設計正是這樣,當你達到無為的境界,怎樣的作品都能創作出來。無為並非甚麼都不做,而是做,但不強迫要達到甚麼。佛家也是這個道理。」說到這裏,姚仁喜強調自己其實不懂佛教,都是聽說回來的。話雖如此,他繼續分析:「修持觀想也是這樣子,把情緒及周遭環境對你產生的反應分開,不要去介入、變成你自己要解決的問題。」當然,一切仍是「聽說」的,就連學佛、篤信藏傳、替上師翻譯的事,他說隨便 Google一下便成了,用不著反復提起。
前面談到恐懼,姚仁喜說一般人總是害怕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很難在觀想的狀態下自處,所以永遠不是很自在的樣子。他定義自在就是自己跟自己相處。這對現代人來說是困難的,因大家都只顧滑手機。他最近看到一個心理學的實驗報道,參與者坐在椅子上,實驗的唯一要求就是不去碰放在一旁的手機。如果他們真的想按的話,椅上有一個通有微弱電流的按鈕,一按下去便會有不舒服的觸電感。正當我們以為常人都會避開不去按,結果卻顯示,短短四分鐘內有百分之六十多的男性竟然主動去「觸電」。「這是很可怕的,我們情願追求不舒服的刺激,都不願沒有刺激。我們寧可傷害自己也無法接受獨處。」
為此姚仁喜建議大家多打坐,他身邊也認識不少修奢摩他的年輕人。「很多人半途而廢是因為他未曾感受到箇中好處,堅持不到便放棄了。無可否認是社會上的刺激太多,翻開時尚雜誌,男的穿得好帥,女的更不用說。推銷的是化妝品、名牌用具。當你明白一切都是PS(圖像修改)的把戲時,又怎會受誘惑?佛陀並沒有傳授一套理論,他更沒有創建一個宗教,他只是把真相如實告知我們。」他相信人並未愚蠢到置真相於不顧這個地步,我們只是選擇性相信某些部分──「無常」便是一個好例子。「我不會狂妄得說我不會死亡,可是每當想到自己的存在雖然終歸會消失,但這一天卻又是long long away(離我還遠),有一下子會忽然不想去思考這回事。」
他又補充,佛教的訓練正是為了讓我們對治這些想法─一開始真相是難啃的,可是了解過後便會變得舒服、順暢,情形跟打坐一樣。當你嘗到這種滋味時,又怎會主動渴求不舒服、痛苦的刺激?

幾塊磚頭 也是佛教建築
有些建築師創作時強調分析性,有些則有點率性隨意,姚仁喜大概屬於後者。他相信情感不一定是負面、帶來障礙的,佛法讓我們看見自己的情感,並學會免於陷入當中的往復來回。「佛陀宣示八萬四千法門,應機說法,也沒有說哪個較好,而且還要視乎不同時候。創作與情感的關係同樣如此。有些人害怕打坐,因為擔心念頭生起,這是說不通的,就像你拒絕做運動,是因為身體肥胖,擔心行走不便。情感是我們在生而為人的普遍狀態下已經存在的,怎樣去梳理,是每個人各自的功課。」 他指出,第一世蔣貢康楚仁波切以捨棄(Abandoning)、轉化(Transforming)及了知(Knowing)三種行為來教導三乘。聲聞、緣覺乘採用的是捨棄,以壓抑來捨棄貪愛;菩薩乘是轉化貪愛,以慈、悲、喜、捨四無量心對治瞋恚、惱害、嫉妒、愛憎的煩惱;金剛乘則是了知,直接穿透本質(essence),單純地覺察它,不造作、不為所動。這三點在他為宗薩欽哲仁波切翻譯的《不是為了快樂——前行修持指引》中亦有論述。
姚仁喜最為佛教徒津津樂道的自然是他設計的農禪寺水月道場。當初聖嚴法師希望農禪寺可以成為台灣真正的景觀道場,最後無論是否信徒,甫進入水月道場都會為她的非凡氣息所懾住,是建構在人間的真正空中花,水中月。「參觀過道場的人都說,心會一下子變得平靜。我站在那裏觀察很多次,不少父母帶著孩子來,本來吵吵鬧鬧的,一進來立刻靜下來。我也聽過不少這樣的故事─想自殺的人走到大殿,尋死的念頭便消失掉。」有法鼓山的信徒認得他,跑過去跟他打招呼,有的還掉眼淚,說農禪寺設計得很美。姚仁喜說他不是謙虛,水月道場他真的覺得建得還可以,有些地方蠻特別,可他必須表明,整個寺廟建築最後呈現的狀態並不是他所能「設計」的。光影透過大殿牆上的《心經》刻字在空中交疊、水池上白雲浮動、潛藏著新舊交替氣息的簡約空間,「那些都不是單純設計便會出現的東西,而是來自諸佛菩薩及聖嚴法師的祝福,還有許多無法說清的因和緣,造就成現在這個模樣。
對於近人對佛教建築興趣漸濃,好一些圖解佛教建築史的書籍都會不期然比較哪種禪風較重、式樣和布局如何最能體現佛陀本懷。姚仁喜不喜歡他們太著重形式,常把禪意二字掛在口邊,倡導符號主義,到頭來是著相了。「佛教建築的目的是要去寺廟的人提起正念,印度靈鷲山不就只是幾塊磚頭而已嗎? 不能說日本禪宗乾乾淨淨的風格才是佛教建築,而藏傳掛滿風馬旗一點留白都沒有的則不算數。南傳不少寺廟就只是在森林裏搭個草房便是了,只要能提起正念,有何不好?」作為台灣甚至是國際上近年最重要的建築師之一,他笑言從來不相信建築物是最重要的─建築物只是建築物,周邊環境有太多無法用物理來表達的東西,它們共同構成獨特的氛圍、不能言傳的眾祐[1],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