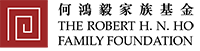林筱魯 城市走出自己的步伐與生命
文:鄺志康 圖:Tim Liu | 2016-10-18

這是個人人討論保育的年頭。
從較早期的皇后碼頭到至今仍未見止息的皇都戲院評級爭議,大眾急切關注的不外乎是如何保護建築能不被拆除。保育從來不只是一句口號、一場抗爭或一篇議論,箇中兩個組成的字相連相依,缺一不可,教導我們學會折衷現實和理想的妥協藝術。「保」與「育」之間的橋樑,更值得大家努力築起。歷史文化的長河往往太深廣,不比人力堆疊的磚瓦親切,資深規劃師、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林筱魯直言,香港人對城市關心得太少,不清楚為何而「保」,更不諳「(教)育」為何物。
「香港至少落後台灣十五年!」
他以硬件和軟件作比喻,復修建築物當然重要,但最後倘只能遠觀,無法使用,對它毫不熟悉,又有何用?他相信故事的力量,以此來連繫古蹟跟公眾的感情。傳承精神就是軟件,是橋的彼端,接上我們忽略已久的文化底蘊。
自林筱魯接替陳智思擔任古諮會主席後,每每遇上保育爭議,在風波中的他卻自有一套欣賞城市和古蹟建築的哲學。去年,有八十年歷史的東蓮覺苑開始復修,他因專業關係,和項目也有一點因緣。「香港人大多只懂李嘉誠、李兆基,何東爵士這名字,陌生得不得了,認識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的,更是少之又少。」關心東蓮覺苑,非關財富,而是那裏彰顯出一個大家族對香港的貢獻及意義。苑內最令他感興味的是一系列「符號」,彷彿Dan Brown的小說。為甚麼那裏有一個可能來自韓國的八卦?為甚麼柱頭有這種像雙龍吐珠的紋飾……「當年找來了一位剛畢業的建築師,年輕人有大家族的支持,自然施展渾身解數,所以現在看起來才有這樣的配搭。」他打趣道,自己不是正常人,動輒可以坐上半天只為欣賞這些小細節,絲毫不覺沉悶。
算起來,是自幼已經開始建立這套哲學了。
生命是任我們去尋找的
林筱魯形容幼時貧乏,但不貧窮。母親攜兄姊來港,後來在家人支持下開了涼茶舖,「她是位強悍的女性。」父親雖喜愛讀書,人也聰明,更寫得一手好字,可惜戰時無力再升學,於是選擇當茶樓掌櫃。兩位都是早出晚歸,大家聚少離多,假日才難得一起吃飯,他自幼便是在這樣的環境成長。他是么子,對上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姊姊。那時候還有一群表兄弟姊妹,都是姑母收養,大家一同長大,不分彼此相互照應。「還記得中四那年我離家出走,到女朋友家暫住,她的父母第二天還讓我坐在一起吃香腸煎蛋。」那是他前所未有過最棒的一餐,因為充滿家的感覺。
他相信正因為得來不易,我們才會更珍惜。小時候要待過時過節才有雞吃,現今都市人早已視殺雞宰牛為理所當然;以往小孩子和長輩同枱用餐,要待長輩先取菜,現在則是父母服侍子女。睡覺是和兄姊一起的,有時睡在床底,要看店的時候還得直接在店裏搭一塊床板睡,醒來才發現頭上長了瘤,人倒在地上;還有辛苦六個星期不搭電車只為節省三毫子去買麵包……凡此種種,已是他生活一部分,他不覺得特別辛苦,相反還無形中賦予他自由探索的空間。「我便開始明白,生命就是任我們去尋找,找到的便屬於自己。」開始接觸宗教,是源於他四姑媽。他很好奇,怎樣姑媽一邊拜佛一邊罵人;桌上既供奉佛祖、觀音,又有大聖爺和關公。「我是問題兒童,不懂的便四處去問人,也不怕人家怪我多事。」
童年便這樣懵懵懂懂過去,也談不上對心靈有甚麼特別的渴求,反正生活就是如此。直到1993年到武漢參與規劃工作,內地當時仍相對落後,因工作關係林筱魯和同事在地盤住了五天貨櫃箱,每天只吃飯盒。後來回到市中心的酒店,用餐時他高興地說了句:「終於有一頓正常的飯了!」旁邊一位當地的年輕人立即反駁,飯盒裏有魚、有肉、有菜,如何辛苦了?當下他立刻反思,原來自己一直從未體驗過真正貧窮的滋味--即使幼時再窮也好,吃的總算是米飯;到了內地,有人一生只能吃稀飯,有的甚至連稀飯也沒有。「此後我有不同機會到各地工作,還記得有次去印度,當地那種不公義、不平等的氛圍,不需走得很遠,一下飛機便感覺到。回來後我只覺得大家在香港真的是身在福中,對生命的反思更加強烈了。」
獅子山下精神何在?
所謂獅子山下精神,人人自強不息,守望相助。舊時強調里仁為美,但現時家庭、社會結構已漸漸轉變,幾乎沒有甚麼特別的鄰舍感覺了。林筱魯認為,城市越發達,資源越來越多,人際關係自然會相較以往疏離。「為甚麼大家住公屋時可以夜不閉戶,互相照顧對方,因為生活模式的選擇不多。當城市結構改變,以往預期沒有的東西出現得越來越多時,便會開始強調『我』,就像現在強調私隱一樣,『我』要安全嘛,於是只好關門上鎖。現今一代太著重應該要有甚麼、想要甚麼。」
「香港的特色是人口密集,我們經常把社區掛在嘴邊其實是自欺欺人。當大家最接近的是對方家裏的閘門時,社區聯繫自然薄弱。我們住在二十五樓,自然不會打開窗戶朝對方大喊。通常最能體現社區聯繫的反而是街市,街坊鄰里聚在檔口談天。其實外國城市同樣面對鄰舍關係薄弱的問題,當大家情願拿著一塊電路板來溝通的時候,還有甚麼可以說?」林筱魯坦言,到這刻仍無法全然接受這種模式,但早已見怪不怪。 倒教他不解的是香港最近潮興「慢活」,他著我們反問到底能否真的做到慢下來,那邊嘴上說慢,手上卻在滑手機。「這可能是一個很精彩的年代,但我真的沒法去評斷它。」現象既已造成,改變它亦非規劃師的職責,首要任務是如何在當代語境下回應這個城市。
這是甚麼鬼地方!
訪問前滿心歡喜以為林筱魯心目中應該有最喜愛的理想城市,他的回答是,雖有強烈個人喜好,卻無法挑選出來。「我只能說我不喜歡一個城市的哪些地方。以深圳為例,我不喜歡,因沒我要求的人味;它太新了,缺乏歷史文化沉澱的氣息。好了,那紐約、倫敦文化氣息濃厚了吧,可是兩者的建築物同樣有其乏善足陳之處。」八十年代他去紐約,街上治安差,環境也不見得是好,第一個印象是:「這是甚麼鬼地方!」七十年代他在英國里茲(Leeds)讀書,當時年輕抱著到宗主國朝聖的心態,怎料一到埗,通訊設備、暖氣設施都……換來的又是一句「這是甚麼鬼地方」。
不過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他同意紐約、倫敦的深厚文化歷史仍是值得我們借鏡。「從文化大局而言,我希望香港有朝一天不是中國人的香港。現在看到的第一流世界城市的特性,正正包含多元文化衝擊,各種機會主義摩擦不同火花,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文化特性最終會反映在建築物上,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捷克首都布拉格以東的庫特納霍拉(Kutná Hora),人骨教堂(Sedlec Ossuary)、聖芭芭拉教堂(St. Barbara’s Church)……他從未在其他地方看過這麼多保存良好的中世紀哥德式風格建築。後來他問友人為何如此,友人說因為窮,沒錢改建。八十年代他一口氣逛了許多中國古城,例如麗江,後來再去也不是那個模樣了。他不打算譴責,世界運作自當如此,但從個人感受而言,失去了便是失去了。發展絕對未必是硬道理。
現在每逢到新城市參觀,林筱魯必定會去街市,觀察當地民眾的消費,其次是醫院,再來是坐在路邊,花兩、三個小時欣賞街景,看看到底大家的衣著如何、談吐如何,最後才是不同建築物。「對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從社會人類學角度看待一個城市,例如倫敦有倫敦的步伐,香港有香港的,而步伐的快慢會直接影響城市以某種形式存在,又再繼而推動市民的生活態度。假如今天你要我離開香港,回到里茲定居,那肯定要好幾個月才能重新適應。步調不一致的人是無法跟那個城市有真正接觸的。」若問林筱魯的城市審美眼光,答案一定是從生活態度入手。一般人浮泛地分析哪幢建築最漂亮,是因為他們沒打算深入了解。香港是個美麗的城市,怎樣發掘它的意趣、韻味,端看我們作何取捨。四十多年,才摸到了一些門路。他微笑說,要學習的還多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