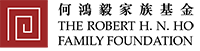蔣勳 :擁抱生命大美,在亂世中修行
文:鄺志康 攝:Tim Liu | 2016-07-29
常有人說時代混亂,究竟背後有何思考?若問蔣勳,他大概會回答,人心浮躁不安,卻又天地有大美。身兼作家、畫家、詩人,他的名字,早已跟美這個概念牢牢緊扣。生活感悟,是他提煉人生美學的精純能源;《孤獨六講》及《夢紅樓‧微塵眾》系列,是他佈道的材料,教曉我們如何在生存及生活間自在擺蕩。一年多前搬進池上,接上台灣濃厚的鄉鎮情懷,揮筆而下的,是一道向碩果僅存的土地倫理致敬的宣言。
在這之前,蔣勳出版了《捨得,捨不得──帶著金剛經旅行》。從歷史角度看,每個時代自有其不安的根源。他親近《金剛經》,因為經中詰問如何在生命中不驚、不怖、不畏。例如現在他坐飛機,一碰到亂流便心慌著急,更不要談對生命徹底了悟。拾方藝廊編採隊伍早前往台灣,首站跟蔣勳老師見面。感謝他分享擁抱生命大美的要訣,為我們揭開深度採訪之旅的序幕。原來修行到了最後不是空談理論,而是回到生活。這,是美學大師的修行功課,也是微塵眾肉身要真實面對的最根本問題。
社會越動盪 越要做功課
外在環境總會讓我們恐懼、害怕。沒有人曉得下一刻會否發生地震、戰爭、飢荒。可以猜想,二千五百年前,驚、怖、畏已是常態,否則佛陀不會宣講《金剛經》。有情眾生擔憂的是甚麼呢?生老病死──身體哪一天決定要死亡的話,我們沒法控制。蔣勳父親離世時,他覺得驚慌;母親往生時,則感到痛苦。這些情緒反應,讓他意會到內在狀態很脆弱,修行仍有不足之處。所以他每天堅持讀四十五分鐘《金剛經》。有人問他,既然已經爛熟於胸,為何還要如此。他說,會背、會唸,跟做不做到,是兩碼子事。「佛經說『信受奉行』,你相信、感受、尊奉,最後在生活裏實踐。修行路很漫長,各有快慢遲早;如果身邊偶爾有朋友不進反退,感覺好像他墮落了,也不應該嘲笑,畢竟要怎樣的因緣具足才能讓人在修行路上走得更穩,我們都無法判斷。應該多點鼓勵,互相彼此扶持。」
越動盪的社會,越是做功課的好時機。
人生太順利,一生沒多大波折磨的人,難得道果。蔣勳非常欣賞剛去世的作家楊絳,從她的《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等作品,讀到諸般關於文革時期的描述。說實話他連想像也不敢,「一個被污辱到那種程度的女人,換了是我,被剃光頭髮,每天給拖出去批鬥,能不憤怒嗎?」近年楊絳的書給他無比力量。即使承受謾罵、遭折磨 ,她仍然保持安定。他聯想到《金剛經》中佛陀憶往昔為忍辱仙人時,歌利王割截其身體──「我於爾時, 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 無壽者相。 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身體一段段被切開,卻了無瞋心,坦然承受,在蔣勳看來,是了不起的功課。「任何打算在修行路上前進的朋友,不能對社會抱有怨恨;而是面對動盪的大環境,仍能撫心自問:我的功課做得夠不夠好?」

佛陀在菩提樹悟道,到鹿野苑初轉法輪。蔣勳一直覺得那是個美麗的地方。首次去印度時,他給嚇到了。無數人在瓦拉納西(Varanasi,古時鹿野苑所在之處)的恆河河畔進行火葬儀式,他坐在船上,到處是人和貓狗的屍體。佛陀當時正正在這種環境下傳法,相較之下現在有漂亮的課室,設備充足。「我敢不敢在殯儀館上課、在醫院的臨終關懷病房上課?敢不敢到人性最敗壞的地方去?佛陀給我最大的鼓勵,是我的修行能更靠近他所做的。」
修行是你一無所得
年輕的蔣勳,會到寺廟閉關,他覺得這樣和出家人一起,很了不起。今天回望,那只是自以為成功,是虛妄的。「一下山我便動心了。」修行不應和生活割裂,是他反覆強調並堅信的。兩年前台北捷運的隨機殺人事件,四死二十四傷,震驚世界。民眾憤恨難平,四月底法院判兇手鄭捷死刑,五月執行。蔣勳說,念《金剛經》念得最慎重的,是鄭捷槍決當天。聽到消息後,他頓然覺得有很多東西放不下,然後為他念了一遍。「大家相信槍決能解決問題,其實並沒有。我們沒有能力根治人性深處最跟自己過不去的部分。只看到逝者痛苦,卻不知行兇者在受甚麼苦,也許他忍受的苦更大。我很同情死傷者家屬,但最後還是要回歸到,『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這是修行的核心價值。」他中學時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喜歡讀《聖經》,到現在親近佛經,慢慢了悟到即使沒有神在面前,還是要修行。 「『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佛陀過去生跟從燃燈佛,形容自己是一無所得,仍然得到授記。這很了不起,試想像你在大學努力唸書,然後跟教授說,其實甚麼也沒學到,就這樣去拿畢業證書。」「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少年蔣勳讀不懂,因為那時還未謙虛到能夠幫助任何一個人的忙。《金剛經》在他眼中,徹底得近乎不可思議。若以為有所收穫,反倒成了自大。他分析「佛」這個字作為Buddha (覺者)的翻譯,那代表著人的否定。修行時我們暫時是人身,可一旦到達涅槃,一切都得消失。
蔣勳認為,很多人雖然讀《金剛經》,但執著跟放下的微妙界線,很難拿捏得準。「『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本身就是矛盾的--不要執著,卻又隨時身處愛恨當中。這部經典的偉大處,在於它太了解人生本身流動的狀態,要求我們不斷修正、思考自己。修行是永遠對自己的超越。」《金剛經》有一段四果離相的對話,朋友常對他說,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及阿羅漢四種果位很難理解。「那是一段永無止境的路。」他提到存在主義受佛教的影響,強調個人邁向超越,如同菩薩一樣,從初果、二果,一直到菩薩,最後成佛。若以為得到甚麼東西,達到甚麼地位,其實那刻你已經死亡了,再也沒法往前走。「一旦得意於某種事物,很快便會失去意義。『煩惱即菩提』,智慧是要在煩惱中尋找的。倘若我今天沒有愛恨,甚麼也感覺不到,也自然沒有修行的意義。」

在煩惱泥漿裏找佛法
世間無常,天災無情。不久前遠方發生大地震,蔣勳看見災民臉上痛苦的神情,不由得想起《維摩詰經》有云,「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眾生要陷入泥漿裏才會渴求佛法。德國作家赫曼.赫塞(Hermann Hesse)撰寫的《流浪者之歌》(Siddhartha),主人翁悉達多,其實就是暗喻佛陀。小說裏有賭場、妓院,悉達多更曾退失道心,沉迷女色,聚妻生子。「東方人不敢這樣寫佛陀。作品當時很震撼,影響非常大。佛陀不通過逃避人生來修行。我們則太容易便逃避了,找個山頭,閉關七天、十天,然後自我感覺良好。」
可是一出門,隨時會有像「小燈泡」那樣可愛的小女孩,頭顱無故被砍斷。蔣勳著我們反躬自問,面對這種世界,應該如何修行?「日本人的地藏信仰比觀音信仰還要深,因為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這話很美學。可是看看我們,先不談發願,連到醫院、監獄修行都不敢。那個距離還很遠。」莫可名狀的詭事、層出不窮的殺人事件;傷痛和悲憤與民眾伴行。台灣過去兩年的發展讓蔣勳頗感不安,一次又一次見證人類內心深處最受苦的部分被誘發出來。「如果單純因仇恨而殺人,還是容易防範的。」但找不到原因的、隨機發生的悲劇,彷彿越來越根深蒂固於人性中,我們又何從理解?

我們不能避而不談死亡
生死之事,華人諱莫如深。民族文化間的差異,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答案。印度之所以為蔣勳帶來震撼,因為死亡是如此赤裸暴露在人前。起初他碰到街上有狗在啃屍體,很不自在,忍受不了,還問警察能否處理一下狀況。警察伸出手,說有三百盧比便可,死亡頓然變得絕頂荒謬。「儒家有『未知生,焉知死』的典故,小孩子過年前一兩個月不許說跟「死」同音的字⋯⋯印度則把死亡視作悟道過程的必經開端。」他在西藏目睹天葬,天葬師把亡者的肉切下來,骨頭用鎚頭砸碎,讓老鷹帶到天上。那一刻他大概就要掉眼淚。「我們過份迴避談論死亡,以致當它到臨時,往往已是手足無措,甚至表現得虛假。台灣有這樣的現象──親人出殯,大家會哭會唱,哭不了唱不了的,便花錢請人來唱。這已變成表演藝術了,唱得好的跟唱得不好的,價碼會有分別。 」
蔣勳在法國留學,受沙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義影響。他有一短篇小說叫《牆》(Le mur),主角因為不肯供出同伴的下落,被判死刑。和他一起的囚友,面對質問及逼供。死亡如此接近,他終於嚇得尿褲子。「人打從一出生便開始靠近死亡,可是我們總覺得這事跟自己的無關。苦、集、滅、道四聖諦,協助我們從了解死亡開始,那是一生必須的功課。」父親逝世,蔣勳首次經歷死亡,六兄弟姊妹,驚慌惶恐,不知如何處理;後來母親往生,因為之前有所歷練,心理準備多了,可是依然會傷心痛苦;2001患上心肌梗塞,生死懸於一線,最後還是活過來。「雙親給我的功課已經完成了,接下來的一定是跟自己的身體告別這回事。我不曉得和它相處七十年後,將來會尿著褲子,還是很優雅地告別。」
池上的溫暖 肉身的觸感
大自然懷抱中的鄉村,同時也是人文育成的基地。2014年底,台灣好基金會邀請蔣勳到台東縣池上鄉擔任「池上藝術村」的總顧問及首位駐村藝術家。一年半過去,他創作了二十九件作品。碧綠的林木草苗,粉艷的野際炎陽,一大抹金黃欲滴的油菜花海,收攝無盡自由的鄉土風光。《池上日記》及 《池上印象》新書系列,紀錄了他師從大自然的心靈感動。
蔣勳說,池上的人口大概六千到八千多人,因為沒有高中,十五歲以上的學生都會離開池上,人口是一直減少的。初到池上,他來到一所舊教師宿舍,跟童年的家很像,勾起兒時珍貴的回憶,於是二話不說搬進去,準備畫畫。第一晚他工作到晚上八、九點左右,肚子餓了,打算上街用餐,怎料一家店都沒有開。居民問他,怎樣這個時候才來,餐廳七點都已經關門了!他體驗到農村跟都市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池上鄉民的人生跟太陽連繫在一起,原來小時候在書上讀到的「日出而作,日入面息」是如此真實不虛。「過去農業社會很重視二十四節氣,可是如今生活在大都市的人根本不知道是甚麼一回事,不再理會春分、秋分的分別是甚麼。我曾到埃及阿斯旺(Aswan),紀念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的阿布辛貝神殿(Abu Simbel)有一道長廊,每逢春分跟秋分這兩天,陽光會精準投射在法老王的像上。古埃及人很清楚太陽在黃道上的移動變化,了解大自然與人之間的秩序。」

池上農民大概在立春後開始插秧。那段日子多數會下雨,泥土濕潤,是最佳時機。農民會互相幫忙,合作把事情辦好。蔣勳深受這種守望相助的精神感動,沒有人是自私的。到秋天時大家要搶著收割,因為時間同樣緊湊,慢一點的,稻作便會腐爛。「這種土地倫理關係,在台北已經殆盡,大家認為只要自己活著,便已足夠。」他回憶童年時 ,家門都不用關,跑來跑去,安全得很;可惜現在,一有人靠近身邊便害怕,因為不曉得他會否是另一個鄭捷。大眾活在恐慌當中,要到處防備。「在池上生活自有一套規則,我要尊重那裏的自然秩序。」後來當他清晨起床,常常發現宿舍門外放了一大堆絲瓜青菜。追問鄰舍,大家都不知道是誰放的。沒多久便有人「罵」他這台北人真奇怪,家裏種多了瓜菜,很自然會分給鄰居,他只管享用就是了,還要尋根問底?
「不論台北也好,香港也好,我們已沒有在土地勞動後分享成果的習慣了。更痛苦一點說,連親人之間也不再如此。像早前有少年竟然為了六萬新台幣,將母親割喉殺害,人與人的溫情、倫理,一下子喪失了。」蔣勳還記得二十五歲去巴黎留學前,所有飯菜是母親煮的,家中六個小孩的衣服是她做的,連被也是她親自繡的。到了他差不多五十歲,已經成為東海大學的系主任,有一次母親來探他,竟然在學生面前直呼他的小名「弟弟」,還說:「你趟下來,我幫你挖耳朵。」「耳朵是很敏感的部位,不能隨便讓人家碰。兒時我很享受讓她挖,還很快便睡著。那一刻我真覺得她有點離譜,但像她這樣在鄉土生活慣的人,反而奇怪,兒子你幹嘛要端架子?人就不能用最溫暖的方式接觸嗎?」後來那批見證他母親挖耳朵的學生,跟他關係好得不得了,「他們都笑翻了,老師的形象完全被顛覆。」
蔣勳相信這是民間智慧的體現。他在關於身體美學的著作中,常談到擁抱這個概念。在儒家文化的氛圍下,touch (身體的接觸)是不大可能的動作,可是明明五感又得依靠觸覺方可達到彰顯親密感情的高度。「台語有時會叫太太做『牽手』(khan1-tshiu2),因為互相touch 的才可以做親人。」母親去世時,他特別痛苦,因為跟她的touch 很多;而父親是嚴肅的人,他們較少身體接觸。「在華人社會,孩子多親近母親。這種touch 不是講求邏輯的。」
「擁抱」這個詞語,蔣勳讚不絕口──那是手的包容。政客最愛談包容、求同存異、放棄對立,他覺得這些都是假的:一個人把對方抱在懷裏,不講一句大道理,那才是真包容。我們能否在別人最無力、最需要安慰的時候,把體溫分享給他?「其實並不是大家現在不touch,只是關係換了跟手機發生。」在池上那段日子,他看到鄉民互相拍來拍去、打來打去。那種數量豐富的touch,教他領悟到,也許現代人要修的不止是知識理論、思維能力,而是學會從身體行為中找回人際關係最本質的東西。儒家太強調思維和理性了,古印度早在佛陀之前已探討感官系統的巨大力量,西方哲人也是如此。「佛教是最現代的哲學,它並不只是教導我們要跪在寺廟裏五體投地。」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時代,因果糾結絲連,無由分判。誠如蔣勳所言,如何坐在像鄭捷這樣心靈痛苦的人身旁念《金剛經》, 才是我們最逼切要思考的課題。